代孕如何改變醫學 -「正常」被視為需要解決的問題
作者:瑪麗·哈靈頓
1954年,俄羅斯科學家成功地將一隻小狗仍然活著的頭嫁接到一隻現有的成年狗身上。我最近偶然發現了一張由此產生的恐怖照片,我認為這將永遠困擾著我。但為什麼它令人沮喪?
那些不受資產階級道德束縛的人可能會簡單地說「哎呀,這是不自然的」來解釋他們對雙頭狗的本能厭惡。當然,這是事實,但那些試圖堅持精英道德正統觀念的人將很難提出同樣的觀點。今天,「自然」的概念被高度政治化。
這使我們在應對生物醫學技術的加速發展方面處於落後地位。它帶來的許多進步並不像雙頭狗那樣明顯怪誕。但即使(或特別是)他們打扮成民權的勝利者,這種不安也像難以表達的那樣深刻。
周末爆發了這樣一場令人不安的辯論,當時《衛報》刊登了一篇關於科里·布裡斯金和尼古拉斯·馬吉平托的長篇文章,這兩名紐約男子向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提起了集體訴訟, 指控紐約市。他們認為,與女性同事不同,他們的健康保險不包括不孕症的試管嬰兒或代孕,這構成了歧視。在他們看來,雙方都是男性的事實相當於「社會性不育」,因此他們的醫療保健應該為妊娠代孕的費用提供資金。
代孕是一個敏感的話題,特別是涉及同性伴侶的地方。畢竟,有真正的活生生的人類孩子,以及慈愛的父母。更複雜的是,提出問題很容易被解讀為——或者實際上被解讀為——對同性戀者的公開攻擊。
但這個問題需要得到解決。因為布裡斯金和馬吉平托以平等的名義所呼籲的,遠遠超出了對家庭的渴望。這是醫學的根本轉變,從一門尋求「恢復正常」的學科,到一門將「正常性」視為「需要解決的問題」的學科。當我們仔細觀察時,這種超人類主義的轉變實際上攻擊了同性戀權利本身的概念基礎。
「這是不自然的」在今天不太站得住腳的一個原因是,「受過教育的」道德共識認為「自然性」的主張在很大程度上是偏執的反對者(跟蹤馬)。這並非完全沒有根據:例如,種族正義的歷史提供了大量科學的理由來證明為什麼權力失衡實際上是「自然的」。
但是,從這一點可以看出,相反的情況是正確的,而且,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聲稱的那樣,「沒有什麼是自然的」?實際上,這是精英們的共識。然而,問題在於,某些「自然」遠非社會建構的、任意的,或者是由沙文主義者為壓迫婦女或少數民族而發明的。
像其他物種一樣,人類具有許多一致的生理特徵,發育模式和行為,經過數千年的進化。行為學和系統發育學等學科研究這種模式,生物體的整體形式有時被稱為其「生物計劃」(biopolan)。而人類,就像其他生物一樣,有一個生物計劃。
我們可能會質疑其外在,但整體模式甚至對小孩子來說也是顯而易見的。事實上,「正常」的樣子通常是從觀察中推斷出來的(正如大多數父母的發現),幼兒可以被教導不要對異常值做出大聲的評論。也不僅僅是關於我們的形狀。有些模式是發育性的,比如青春期,有些模式,比如性別二元,是我們作為一個物種的延續的基礎。在正常情況下,人類生物計劃需要一個小的和一個大的配子來製造一個新的人類
- 加上一個活生生的人類女性九個月的妊娠期。
布裡斯金和馬格吉平托要求傳統醫學中的「正常」
- 他們不能懷孕的事實,因為他們都是男性
- 不被視為一種自然限制,而是一個須要治療的「醫療保健問題」。
我不想重複關於我們中是否有人對遺傳後代有「權利」的爭論。我所關心的是,當你將生物計劃本身重新定義為一個醫學問題時,更廣泛的醫學科學領域將如何變化。實際上,你正在把醫學科學從內到外化,所以人類的「正常」不再是所期望的醫學最終狀態的指南。相反,它是人類慾望無限輸出的障礙。
這個前提以技術樂觀主義、右翼自由主義的形式為基礎,支撐著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的實驗性神經連結技術,馬斯克說,這項技術最終將像「你頭骨裡的FitBit」。同樣,它支持美國政府最近決定將20億美元用於生物技術研究,這些研究將能夠「為細胞編寫電路,並以與我們編寫軟體和電腦相同的方式對生物學進行可預測的程式設計」。
克服人類(性別)生物計劃是跨性別權利的核心前提,例如,宣導者談論兒童經歷「錯誤的青春期」。它還支持「生育平等」的社會正義論點,其中代孕被視為合法使用技術來克服正常人體生理學施加的不公正限制。
技術烏托邦主義者和社會正義者都忽視(或選擇忽視)的是,將正常的人類有機體視為一系列醫學挑戰伴隨著金錢和權力的層次結構。尖端的實驗醫學是有代價的——既要給潛在客戶,有時也要為它的測試物件付出代價,就像一個年輕人在實驗性手術後死於壞死性筋膜炎一樣,用自己的結腸給他製作了一個新陰道。
特別是在代孕的情況下,這意味著富有的男人和女人,如布裡斯金和馬吉平托(或者實際上是埃隆·馬斯克的嬰兒媽媽,歌手Grimes)可以利用無限的超人類主義藥物所打開的潛力,來逃避他們自己的生理限制,或者只是(如Grimes的情況)將「正常」母性的艱苦和危險外包給其他人。與此同時,妊娠的「工作」,連同其侵入性手術、終身後續併發症甚至死亡等不小的風險,都被外包出去——通常是外包給較貧窮的婦女,而且往往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剝削條件下。
當然,這些不對稱並不是同性委託伴侶所獨有的。代孕總是有傳播這種虐待的風險,即使委託的父母包括女性。但是,如果代孕以充滿道德問題且極易受到剝削的方式將商業和醫學結合起來,那麼其超人類主義者的重新建立在結構上就以代孕的存在為前提。在超人類主義的框架中,有一對全男性伴侶渴望遺傳的孩子,「治癒」需要一個肥沃的子宮
- 女性對此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是無關緊要的。
但是,在保障措施下,只有女性同意才能參與?布裡斯金和馬吉平托從賣淫中打出一個類比來論證這個論點。然而,與此相反,50年的性革命應該告訴我們,權力不對稱的「同意」是多麼脆弱。不乏來自性產業倖存者的證詞,關於許多人在表面上「自願」的過程中所經歷的恐怖。回顧一下最近MeToo的大量湧現,應該會提醒我們,在財富和權力存在巨大差異的地方,即使在商業交易之外,「同意」也往往是流氓的憲章。
將MeToo擴展到生育「服務」並不需要太多考慮。也不需要更多時間就能看出它如何適用於身體其他部位的「自願」商品化。婦女已經向生育行業出售卵子;為什麼我們不應該出售腎臟或部分肝臟,只要每個人都同意?
如果我們接受超越生物物理極限的基本正義,那麼我們能做些什麼就沒有理論上的界限。我們不能反對巴西外科醫生用魚皮為跨性女構建新陰道——
因為我們已經接受「不自然」只是偏執的反對者 (跟蹤馬)。從這裡開始,我們幾乎沒有理由反對「升級」,這更徹底地改變了人類的「正常」。
你可能會嘲笑這一切都只是歇斯底裡。不過,回想一下,關於安樂死的「滑坡」論點曾經被駁回為誇張。然而,根據比利時和加拿大的案例,這些論點不僅準確,而且不夠誇張。
當然,為了同性伴侶的平等和家庭生活,冒險是值得的嗎?相反,我們應該提防似乎基於同性戀權利的超人類主義論點。因為廢除這種世界觀根源上的「自然」,已經反噬那些首先為這種變化歡呼的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
同性戀權利的基礎是同性吸引是自然和天生的。但是,如果沒有「自然」這樣的東西,這種理由就會突然被消除,讓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再次容易受到改變行為的壓力。事實上,這已經經由跨性別行動主義發生:在那裡,如果同性戀者拒絕異性的「同性戀」伴侶,他們現在經常被指責為偏見,而他們的(自然的,正常的)同性取向被重新歸類為「生殖器戀物癖」。
大多數訴諸代孕的同性戀或異性戀者這樣做是為了滿足他們對愛和照顧孩子的渴望。我們應該認識到,這從根本上說是人類深處的願望。但是,如果愛是將人類社區凝聚在一起的粘合劑,它也可以推動具有更廣泛負面影響的選擇。代孕,特別是代孕作為正常生物學限制的「治療方法」,就是這樣一種選擇。
它為一種無限的、利潤驅動的放鬆對人類有機體的管制打開了大門——歸根結底,這一驅動力將主要有利於大型生物技術公司。而只短暫停留在愛和正常的溫暖光芒。在那之後,我們進入了怪物的領域:殘缺不全的兒童,人類/動物嵌合體,配子和器官摘取以及醫學實驗,僅舉幾個例子。
如果我們繼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男同性戀者和女同性戀者最終將失去(最近才獲得的)自然同性戀權利。如果這已經夠糟糕了,那麼在商業生物醫學的勝利以及隨之而來的一大群多變的恐怖之後,它似乎變得微不足道。
How surrogacy is
transforming medicine
https://unherd.com/2022/10/how-surrogacy-is-transforming-medicin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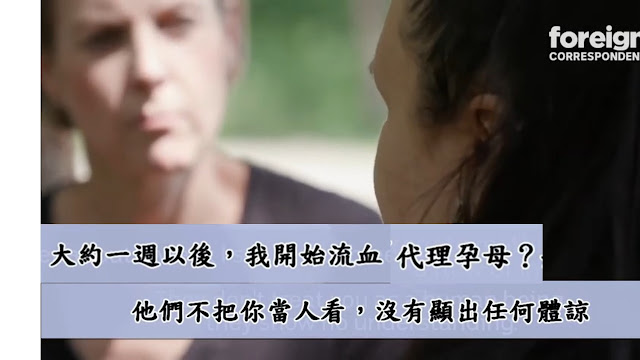



留言
張貼留言